
我躺在洁白的病床上,刚刚发生的一切仿佛不真实。床的两侧布满结实的金属扶手。我的身体仍然无法平躺,侧身蜷缩的姿势与我松弛的体型相得益彰,起身也变得十分艰难。我紧握扶手,以此为支点挪动双腿,终于艰难地移动到床尾的出口,但床沿凸起了一段,我无法稳稳踏在地上。
"扶住我,先在床沿坐下 30 秒,然后站起身 30 秒,感觉稳定后才可以动。"护工扶着我的身体,另一侧是先生的臂膀,我缓缓探出病床,目的地是几步之遥的洗手间。
借此机会,我停下来仔细打量镜子中的自己。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,还是一身蓝花的病号服,松松垮垮地坠着,勾勒出我凸起的梨形身材。不同的是,产后护工换给我的这套病号服花纹更新,质地更厚,仿佛提醒着我不能受风着凉。
后背的腰痛并没有随着婴儿的出生消散,骨盆扭动时依旧发出咯咯的疼痛,如影随形——只是我的肚子里少了一个大肉团。这一发现让我既不适又悲伤。刚刚,这个肉团子刚刚被一嘬奶粉填饱。离开母体后,她被一股力量抛入这个世界,她感到极度不安,便又沉入熟悉的黑暗中安稳入睡。但这个最该休息的夜晚,我却一直咳嗽,毫无睡意。刚才的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,就像一剂强效肾上腺素,让我不禁靠在床上回想。
我想起淋浴房天花板上的浴霸,那里暖光肆意流淌到她身上,她双手扶着湿润的墙壁,巨大的肚子朝下,一边忍受着汹涌的阵?麻醉师到了。"她们问我。
"啊,我要再想想。"我现在还可以忍受这一波波轻微的疼痛。
"麻醉师来一趟,后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"护士说。
"八床,八床的胎心率有异常,胎儿缺氧。"她们很快走了过来,一位助产士伸手进来进行人工破水,就像轻轻捏破一个气球一样,一股暖流瞬间流出。我只能躺在隔尿垫上,简单地盖了一条单子。

"医生,我开了几指?""两三指。"我突然有些犹豫,这不对,二胎的进程不应该这么慢。如果真的拖到深夜,我不打无痛的话,如何能坚持过疲惫和疼痛的消耗呢?我细细地思考着,万一刚插管,麻醉还未起效就生了怎么办?就在那一刻,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生孩子的勇气。一胎时,我太过于眷顾,疼痛是短暂的,没有体会到疼痛的耗尽。而人一旦把注意力投射到软肋上,就会感到真的软弱起来。

熬过六点,先生连续来电,我无暇顾及。父亲做的清汤素饭不知何时被放在我的床铺上,我哆嗦着无法仔细打开层层饭盒,捣鼓勺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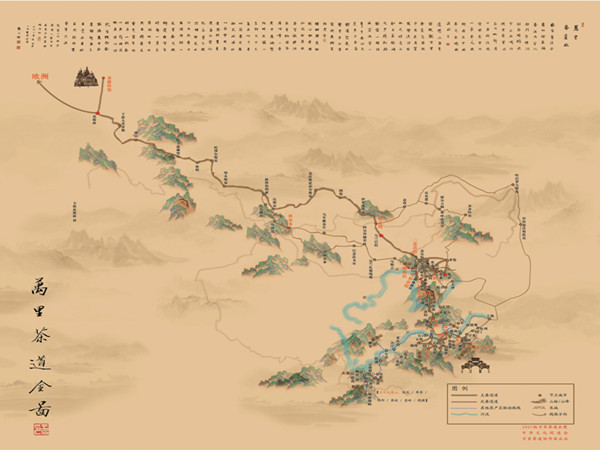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